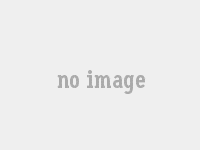叶挺回家成亲
叶挺回家成亲,一九一二年,二块大洋,一张三百块的银票,这就是那个包办婚姻除夕夜的全部家当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乖乖办事,要么断了父子情分 那时候谁也记不清黄春到底多大,十岁,还是十一岁?媒人嘴里,她是拿两个三岁五岁妹妹换来的“床头婆”。
进了叶家大门,她就不能叫阿春,得随着叶家八哥的称呼,改叫“叶家的”那年叶挺才九岁,蹲在院子里看蚂蚁,见她迈过门槛,头都不抬,只说了一句踩坏了兵马黄春吓得往后缩,脚后跟撞得生疼,愣是不敢掉一滴眼泪在那个年代,童养媳的眼泪也是要算斤两的,哭多了,人家嫌你心眼小。
日子过得苦水似的天没亮挑水,水满了天也亮了;灶膛火星子乱窜,烫出泡来,抹把口水继续烧火黄春有时候看着叶挺吃饭,筷子捏得直挺挺,不像在吃饭,倒像是在夹什么东西的命门这人哪里不一样?她说不上来,只觉得他吃饭不光为了填饱肚子。
变化来得快叶挺十四岁那年,剪了辫子,整个周田村就他一个黄春正在井边搓衣裳,听见外面喊“叶家八哥反了”,扔下衣服就往家跑院子里,公公叶锡三举着锄头要打,那条剪下来的辫子像条死蛇黄春脑子一热,扑过去抱住公公腿喊了声爹。
这一嗓子,把锄头喊停了,也让叶挺看愣了神从那以后,叶挺去了惠州府学堂,又去了蚕业学校,后来干脆跑到了广州每次半夜回来,带着股烧纸味儿或者血腥气,塞个油纸包让她转交阿爹黄春不识字,认得那红戳子是“革命党”,她只管藏好,守口如瓶。
除夕夜,公公下了死命令,必须圆房叶挺大摇大摆回了门,身后跟着长辈,腰杆挺得笔直他说这规矩不兴了,公公拿烟袋锅子敲得震天响,声称不进洞房就断绝关系红烛噼啪作响,照得那个“囍”字忽明忽暗门一开,冷风灌进来。
黄春没等他开口,自己掀了盖头看着眼前瘦削的男人,袖口都磨了边,她心里门儿清叶挺愣住了,本以为要面对一张哭脸,或者木头人,谁知黄春静得像井水 “八哥,你走吧”她把这几年叶挺托她藏的二十七块大洋塞过去,又从箱底翻出件男式藏青夹袄。
那是她趁着夜里点豆油灯一针一线缝的,外头冷,得备着叶挺看着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喉咙像是堵了团棉花两个本该同床共枕的人,手里攥着的却是去路和盘缠黄春推了他一把,力道不小,这一推,把叶挺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叶挺走了,没回头。
他哪里知道,黄春哪里是在守活寡,分明是在替他守着这个家,守着一条后路被窝里有个硬物,摸出来一看,是一张三百大洋的银票这哪里是钱?这是一颗心她懂他的革命,他懂她的付出这大概就是那个乱世里,最无声的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