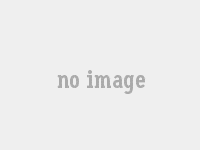自小被放弃,聋哑父母收养我20年,我嫁人后,养父母要断绝来往
养父的双手"爹,您真就这么走了?昨天做好的拖鞋还没给您穿呢"我跪在医院走廊的长椅旁,手里还攥着那双绣着喜鹊的布拖鞋,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小红,别哭了,医生说情况还有转机"一旁的丈夫郑大强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声音里带着些许愧疚。
我叫周小红,今年三十岁,生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小县城,人们还在厂区大院里过着集体生活,家家户户拥挤在四四方方的砖瓦平房里,院子中间有口大水井,每天清晨都挤满了排队打水的大人。
据养父周大山后来比划给我看的,我是被人放在了井边的竹篮里,连个像样的襁褓都没有,只有一张发黄的纸片,纸片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对不起"三个字,字迹像是被雨水浸过,有些模糊不清那是一九八二年的早春,乍暖还寒。
轮到周大山和李淑芳夫妇打水,他们发现了竹篮中的我周大山是县城修鞋铺的师傅,李淑芳在纺织厂做缝纫工,他们都是聋哑人,靠着手艺勉强糊口,生活格外艰难彼时已近四十的李淑芳一直渴望有个孩子,可命运似乎总与她开玩笑。
听隔壁王婶说,她年轻时患过一场大病,从此再没怀上见到我的那一刻,她仿佛见到了希望,眼里闪着光,用手语和丈夫无声地交流着,最终决定把我带回家"一对哑巴收养弃婴?"厂区的邻居们议论纷纷,"这不是雪上加霜吗?"有人劝他们送去福利院:"你们自己都难养活,还收个孩子?再说了,哑巴能教孩子说话吗?"
可周大山和李淑芳却从未动摇。他们把东屋收拾出来,用木箱子和棉被给我搭了个小窝。那个年代,谁家也没有多余的钱买婴儿床,更别提奶粉了。李淑芳每天下班后跑去隔壁李婶家,请她教自己怎么煮米汤、熬稀粥喂我。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捡来的,养父母虽然不会说话,但家里的墙上贴着许多手势图,那是周大山从聋哑学校借来描摹的他们耐心地教我与他们交流,用眼神和手势组成我们家的独特语言那时候,周大山靠着一把修鞋刀,一把锥子,还有几块补丁皮,在厂区门口摆了个小摊。
他的手艺在县城里是出了名的好,补的鞋结实耐穿,许多工人宁愿多走几步路,也要找他修李淑芳除了在纺织厂上班,回家后还接些街坊邻居的缝补活儿就这样,他们硬是把我拉扯大每天清早,我都是被"砰砰砰"的钉鞋声叫醒的。
窗外的天刚蒙蒙亮,炉子上的玉米粥便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那是我生活中最熟悉的摇篮曲周大山的工具箱里总是整整齐齐的,锥子、线绳、鞋楦都有专门的位置他蹲在小板凳上修鞋时,腰板总是挺得笔直,表情专注得仿佛在做一件艺术品。
上小学那年,班里来了个新老师,第一天点名时,老师念到:"周小红?"我站起来应声:"到!""你父母是干什么的?"老师随口问道"我爹修鞋,我娘做缝纫"我骄傲地回答"哦,就是那对聋哑夫妻?"老师皱了皱眉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有人偷偷指着我笑。
放学路上,几个男生跟在我后面,学着哑巴说话的样子:"啊...啊...",还做着夸张的手势"你爹妈是哑巴,你说不定也是个哑巴的种!"一个大个子男生推了我一把。

我气得满脸通红,扭头就跑回到家,我把书包往桌上一甩,对正在纳鞋底的周大山比划:"我不要聋哑人做父母!别人都笑话我!"周大山愣住了,粗糙的手在半空中僵了一下,针线从指缝中滑落他慢慢放下手,眼中闪过一丝受伤,却又迅速掩盖住,低头继续手里的活儿。
那晚,我赌气没吃饭,躲在被窝里生闷气半夜醒来,听见院子里有动静,透过窗户的月光,我看见周大山蹲在水缸边抽闷烟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背影如此单薄,肩膀微微耸动,像是在无声地啜泣虽然我从未听过他的声音,但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周大山送我上学时,塞给我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用鞋样布缝的一个小人偶,脸上还绣着笑容旁边附了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女儿别难过,爹娘爱你"那是他用铅笔头一笔一画写下的,笔迹笨拙却格外认真。
我明白了他的心意,从此再没抱怨过我的家庭反而,我开始努力学习,希望能用优异的成绩让他们骄傲小学三年级,我当上了班长;初中时,我成了学校的三好学生;高中那年,我被评为县里的优秀学生代表,照片还登在了县报上。
那段日子,周大山把我的剪报小心翼翼地贴在他修鞋摊的木板上,每当有顾客问起,他虽然不能说话,却总是咧嘴笑得合不拢嘴,指着照片比划着李淑芳更是逢人便"说",用她那一套夸张的手势,绘声绘色地表达着对女儿的自豪。
高考那年,整个县城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每天清晨五点,我们家的煤油灯就亮了,周大山轻手轻脚地生炉子,李淑芳给我煮鸡蛋、熬稀饭我夜以继日地复习,父母则轮流给我揉肩捶背周大山的手上全是老茧,捶在背上有些硌人,但那触感却是我最大的安慰。

"嘎吱"一声,老旧的收音机被拧开,播报着高考倒计时虽然听不见,周大山和李淑芳却坚持每天这样做,仿佛这是与外界沟通的仪式考试那天,周大山早早地把我送到考场,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壶,里面是李淑芳熬的绿豆汤"考完记得喝,消暑气。
"他比划着,眼里满是期待成绩公布那天,我忐忑地去学校查榜,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在省重点大学录取名单上时,激动得差点晕过去我飞奔回家,远远地就看见周大山在门口张望,看见我的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询问"爹!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边跑边喊,虽然知道他听不见,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周大山看懂了我脸上的喜悦,他放下手中的活计,三步并作两步迎上来,一把将我抱起,原地转了好几个圈邻居们被这阵动静吸引过来,纷纷围观,七嘴八舌地恭喜那一刻,周大山的眼里闪烁着泪光,他对着邻居们比划着:"我女儿,我女儿..."。
我成了厂区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街坊邻居都说:"周小红真争气,给哑巴老两口挣了大脸!"临行前的晚上,李淑芳给我缝了一床新被子,棉花是她攒了好几年的新棉,被面是厂里发的福利布,上面还绣了几朵小花周大山则把他珍藏多年的存折塞给我,上面有一万三千元,几乎是他们毕生的积蓄。
"爹,这太多了..."我推辞着。周大山摇摇头,郑重地把存折塞进我的手里,然后比划着:"读书要紧,别委屈自己。"

我含着泪点头,知道这些钱凝聚了多少汗水——那是无数个清晨的钉鞋声,无数个深夜的缝补灯光,无数个风雨天里,周大山蹲在屋檐下专注修鞋的背影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参加各种活动,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
大二那年,我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认识了郑大强,他是经济系的学生,表演了一首萨克斯独奏郑大强长得高高大大,家境殷实,是个阳光开朗的男生他父亲是市里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家里有一套一百多平的商品房,那个年代,这在我们眼里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们渐渐熟络起来,从同学变成了恋人每次约会,他都会精心安排,带我去校外的小餐馆吃饭,偶尔还会送我一些小礼物——一支钢笔,一条印花丝巾,一本精装诗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礼物显得尤为珍贵大学毕业那年,郑大强带我回家见父母。
他家住在省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客厅里摆着真皮沙发和一台进口彩电,餐桌上的菜色丰盛得让我眼花缭乱席间,郑母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如实相告:"我是被抛弃的孤儿,从小被一对聋哑养父母收养..."餐桌上顿时安静下来,郑父母交换了一个眼神,郑母的脸色明显变得复杂起来:"哦,那真是...不容易。
"回校的路上,郑大强欲言又止。"怎么了?"我问。"没什么,就是...我父母可能有些顾虑。"他低声说,"他们觉得咱们背景差异太大,将来可能会有问题。"我心里一沉:"因为我是孤儿?"

"不全是"他停顿了一下,"主要是你养父母的情况...你懂的,他们认为这样不太方便以后的交往我爸在单位有头有脸的,亲戚朋友都是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如果带着一对...特殊父母,可能会有些尴尬"我站在路灯下,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春风拂过,却带不走心头的凉意"所以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郑大强握住我的手:"我很喜欢你,真的但我父母可能接受不了...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他犹豫了片刻,"要不这样,我们结婚后,就别跟你养父母来往了?反正他们也听不见说不了,慢慢就淡了...等将来我们有了孩子,工作也稳定了,情况可能会好转。
"当时的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居然点了头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未来毕竟,周大山和李淑芳把我养这么大,不就是希望我有出息、过上好日子吗?婚礼前,我回了趟老家看着养父母兴奋地准备嫁妆——李淑芳亲手缝制的被面、枕套,周大山专门做的一对红木小凳子,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们婚后的打算,但看着他们期待的眼神,我怎么也说不出口婚礼那天,郑家大摆筵席,请了近百桌宾客周大山穿着平日里修车补胎从不舍得穿的那套中山装,李淑芳戴上了她年轻时的一对银耳环,笑得合不拢嘴。
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郑家亲友中间显得格格不入——别人推杯换盏,高声谈笑,而他们只能安静地坐在角落,偶尔用手势交流两句婚后,我搬进了郑家位于省城的大房子,有了舒适的生活郑大强在父亲的公司上班,起点就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
我则在一家外企找到了翻译工作,工资不菲

表面上看,我们是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但每当看到郑大强父母和亲戚们谈笑风生时,我就会想起那个永远安静的小屋,想起那双因常年持刀而变形的手我托县城回来的同学给养父母送去钱,但再没回去看过他们渐渐地,连我自己都说服了自己:这样也好,免得他们担心我的生活。
再说,他们听不见也说不了,可能根本感觉不到什么不同直到那个夏天,社区居委会打来电话,说周大山患了肺炎住院,情况不太好电话那头是我小时候的邻居王婶:"小红啊,你爹病得不轻,前几天还念叨着要给你做双鞋呢,你要不要回来看看?"。
我放下电话,手脚冰凉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残忍——我抛弃了那对养育我的父母,仅仅因为他们不够"体面",不符合我现在的"生活圈子""怎么了?"郑大强从书房出来,看我脸色不对"我养父病了,住院了"我低声说。
郑大强沉默了一会儿:"要回去看看吗?""嗯"我点点头,没有抬头看他,怕看到他眼中的不以为然"那...你自己去吧,我这两天公司有个重要会议"他顿了顿,"别耽误太久,下周末我妈要过生日,准备请些领导来家里吃饭。
"我瞒着丈夫和公婆,只说去出差,连夜坐车回了县城清晨的县城依旧宁静,只是那个熟悉的厂区大院已经变了样——许多平房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几栋简陋的六层小楼我熟门熟路地找到了我们的老房子,半路上遇见了王婶,她告诉我李淑芳一直守在医院,家里没人。

医院里,李淑芳已经满头白发,见到我时手都在发抖,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下来她比划着告诉我:"你爹病了一个多月了,一直不肯去医院,说要省钱给你寄过去前天晚上突然喘不上气来,这才把他送进医院..."她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病房。
周大山躺在简陋的病床上,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大圈,但见到我时,眼中仍放出光彩,颤抖着手想从枕头下摸出什么李淑芳帮他拿出一包用报纸仔细包裹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双绣着喜鹊的布拖鞋,针脚细密,显然是花了很长时间。
"你爹日夜念叨你,手都磨破了给你做拖鞋..."李淑芳比划着,"他总担心北方冷,怕你脚受凉"那一刻,我的心如刀绞三年了,我几乎断绝了与他们的联系,只偶尔托人捎去些钱,连个电话都没打过而他们呢?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着我,用他们的方式爱着我。
我再也忍不住,抱住了周大山的手痛哭:"爹,对不起..."周大山用粗糙的手抹去我的泪水,嘴角微微上扬他虚弱地比划着:"好女儿,别哭,爹妈不怪你..."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周大山的病情总算有所好转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回家收拾父母的物品时,我才发现他们生活的窘迫——冰箱里只有几个土豆和白菜,衣柜里的衣服都洗得发白,而床头柜上,却整整齐齐地摆着我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我寄回来的每一封信在一个旧鞋盒子底下,我发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我结婚时的照片,还有一些医院的收据。
翻开一看,原来李淑芳前年做过一次小手术,花了近两千元,可他们从没向我提过

这一切让我无地自容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就因为他们不会说话,就因为他们没有光鲜亮丽的社会地位?当晚回到郑家,我终于鼓起勇气,对丈夫说出了真相和我的决定:"郑大强,我要把养父母接来省城住""什么?"郑大强放下报纸,皱起眉头,"我们家哪有地方?"。
"三室两厅还不够大吗?"我反问"可我父母怎么想?他们会接受两个老聋哑人住在家里吗?"郑大强显得有些焦躁,"再说了,让他们住在县城不是挺好的吗?那里有他们熟悉的邻居,熟悉的环境...""他们需要人照顾,"我坚定地说,"如果你不同意他们住进来,那我就搬出去和他们一起住。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但我知道,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在那个医院的病房里,看着周大山枯瘦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我就下定了决心,再也不要让任何东西隔在我们之间郑大强沉默良久,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出乎意料的是,他最终叹了口气:"你真的决定了?"。
"嗯"我坚定地点头"我一直觉得你不开心,原来如此"他苦笑了一下,"去把他们接来吧,家里有的是房间但你得答应我,帮他们适应这里的生活,别让我父母太为难"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去接养父母回新家周大山刚出院,还有些虚弱,但见到郑大强主动来接他们,老人家激动得双手发抖,一个劲地点头致谢。
看着李淑芳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光滑的大理石台面,看着周大山在阳台上对着阳光舒展筋骨,我的心终于放下了。

起初,生活并不容易郑父母对这对聋哑老人明显不够热情,餐桌上的氛围常常尴尬但随着时间推移,周大山的勤劳和李淑芳的善良打动了所有人周大山主动承担了家里修理物品的活计,李淑芳则做一手好菜,尤其是她的酱猪蹄,连挑剔的郑母都赞不绝口。
最让我感动的是,郑大强开始学习简单的手语,努力与我的养父母交流有一次,他比划着问周大山:"爸,这鞋能修吗?"虽然动作笨拙,但周大山看懂了,高兴得像个孩子,连连点头后来,我们添了个小生命,取名郑小满周大山和李淑芳成了最称职的爷爷奶奶,每天变着花样给小满做玩具,教他无声的手语。
小满竟然在会说话之前,先学会了几个简单的手势,这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血缘或许让我们相遇,但真正的亲情,是那双粗糙的、温暖的、不会说话却能传递一切爱的手它们教会我生活的勇气,教会我爱的真谛,也教会我如何做一个真正有尊严的人。
如今,每当我看到周大山在院子里教小满叠纸鹤,看到李淑芳耐心地教郑母做手工,我就知道,家不在于多么华丽的房子,而在于那些用爱填满的瞬间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有谁真心爱你、等你、牵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