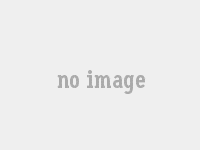燃爆了(猎户救了狼崽的电影)76年猎户救受伤货郎,货郎留包裹说十年后方可打开,
目录:
1.猎户救下狼崽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2.猎户救狼崽叫什么电视
3.猎户救了一只狼崽子是什么电影
4.猎户救了小狼是什么电影
5.猎户救了一只狼
6.猎户救下受伤的狼崽
7.猎户救了狼崽子
8.猎户好心救了狼的电视剧
9.猎户救下狼崽的电影
10.猎户救了狼狼报恩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1.猎户救下狼崽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第一章:雪中誓言一九七六年的雪,来得比往年更早,也更凶长白山深处,风像一头饿了千年的白毛狼,贴着地皮打着旋,把松针刮得呜呜作响,仿佛随时要撕开这天与地之间的一切石山根蹲在自家那座快被大雪埋掉一半的木楞房门口,眯着眼,辨认着风里传来的每一丝声响。
2.猎户救狼崽叫什么电视
他是个猎户,三十七八的年纪,一张脸被山风刻得像老树皮,沟壑纵横他的世界不大,就是眼前这座山山有山的规矩,狼有狼的道,他懂今天这风声,就是山在发脾气,懂规矩的,都该缩在洞里,而不是在外面晃荡可他听见了别的声音,一声微弱的、不属于这山的哀嚎,被风扯得断断续续,却像一根针,扎进了石山根的耳朵。
3.猎户救了一只狼崽子是什么电影
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雪,那身打了补丁的羊皮袄沉甸甸的他抄起靠在门边的猎枪,枪管冻得像根冰棍,又从墙上摘下那把跟了他二十年的砍刀,别在腰后“山根,这天你要去哪?”屋里传来女人担忧的声音,是他的婆娘秀莲“风里有东西,我去看看。
4.猎户救了小狼是什么电影
”石山根的声音跟他的人一样,沉稳,简短,像砸在地上的石头“别是‘跑山’的吧……”秀莲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恐惧‘跑山’是他们这儿对山里那些来历不明的野兽或精怪的称呼石山根没回话,只是把毡帽的护耳拉了下来,一头扎进了那片白茫茫的风雪里。
5.猎户救了一只狼
他循着声音,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坳里走雪没过了膝盖,每一步都像在泥潭里拔腿风把他的视线搅得模糊,只有偶尔露出的黑色岩石和枯树的轮廓,是他熟悉的路标走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他在一处背风的陡坡下,看到了一个黑点。
6.猎户救下受伤的狼崽
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人,蜷缩在雪窝里,身上那件不属于山里的蓝色干部服已经被雪染白,一条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旁边翻倒着一个扁担和两个散落的货箱是个货郎石山根蹲下身,探了探对方的鼻息还有气,虽然微弱得像随时会断掉的蛛丝。
7.猎户救了狼崽子
他把那人翻过来,一张完全陌生的脸,瘦削,苍白,嘴唇冻得发紫,但眉宇间透着一股子书卷气,不像常年在山里讨生活的人“喂!醒醒!”石山根拍了拍他的脸那人眼皮颤动了几下,勉强睁开一条缝,看到石山根这张布满风霜的脸和肩上的猎枪,眼神里瞬间充满了警惕和恐惧。
8.猎户好心救了狼的电视剧
他挣扎着想往后缩,却牵动了断腿,疼得闷哼一声,额头上瞬间冒出冷汗“别动,腿断了”石山根言简意赅他没理会对方的惊恐,山里救人,没那么多客套他解下自己的羊皮袄,裹在那人身上,然后像扛一袋粮食一样,把他甩到自己肩上。
9.猎户救下狼崽的电影
那人很轻,没什么分量石山根扛着他,一步步往回走来时容易去时难,背上多了个人,脚下的雪仿佛也多了千斤的吸力风雪更大了,四周白茫茫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石山根全凭着身体的记忆,像一头老熊,在自己的领地里,闭着眼也知道哪棵树下有窝,哪块石头后面能避风。
10.猎户救了狼狼报恩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回到木楞房时,他整个人几乎成了一个雪坨秀莲惊叫着迎上来,帮他把人弄到火炕上屋里烧着松木,噼啪作响,暖意融融,与屋外是两个世界石山根给那人检查了伤腿,是小腿骨折,骨头茬子没有戳出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从箱底翻出祖上传下的跌打草药,用烈酒调了,一部分敷在伤处,一部分撬开那人的嘴灌了进去。
又让秀莲熬了锅热乎乎的苞谷面糊糊,一勺一勺地喂那人昏睡了两天两夜,期间不停地发着高烧,说胡话石山根和秀莲轮流用雪水浸过的毛巾给他降温,像照顾自家的孩子第三天清晨,那人终于醒了他睁开眼,看到头顶被烟火熏得黢黑的房梁,闻到空气中松木和草药混合的气味,还有身边火炕传来的踏实的温暖,眼神里的惊恐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和虚弱。
“醒了?”石山根坐在炕边,正用一块磨刀石打磨他的砍刀,声音平静无波“是……是您救了我?”那人开口,声音沙哑干涩“路过,碰上了”石山根头也不抬,“命大”接下来的几天,男人知道了救他的人叫石山根,这是他的家。
他告诉石山根,他叫程援青,是个走村串乡的货郎石山根不怎么说话,但秀莲心善,每天好吃好喝地照顾着程援青的身体渐渐好转,只是断腿还需要将养他是个健谈的人,伤势稍好,就开始给石山根讲山外的故事讲大城市里的高楼,讲铁盒子一样的汽车,讲一种叫“收音机”的东西能千里传音。
石山根默默地听着,手里编着新的草鞋,偶尔“嗯”一声,也不知道听进去了没有半个月后,程援根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能拄着石山根给他削的木棍下地走动了他知道自己该走了这些天,他吃的是石家的口粮,用的是石家的草药,这份恩情,他不知该如何报答。
他那两个货箱里的东西,不过是些针头线脑、洋火肥皂,根本不值什么钱离别的前一晚,雪停了月光透过窗户纸,洒在炕上,清冷如水程援青把石山根叫到屋外他从自己贴身的衣物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四四方方,约莫一尺见方,沉甸甸的。
“石大哥,”程援青的声音在寒夜里显得格外郑重,“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包裹,请您无论如何要收下”石山根看了看那个包裹,又看了看程援青他摇了摇头:“救你,是山里的规矩碰上了,搭把手,不图回报。
”“不,这不一样”程援青的眼神里有一种石山根看不懂的执拗和沉重,“这不是报答,是……一个托付”他把包裹塞进石山根怀里,那东西入手极沉,像是包了块铁“石大哥,我还有一件事,需要您发誓”程援青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甚至带着一丝恳求。
“你说”“这个包裹,您一定要替我好好保管但是,”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十年之内,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您有多缺钱,多好奇,都绝对不能打开它”石山根愣住了十年?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程援青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石大哥,请别问为什么。
您只要答应我,十年从今天算起,整整十年之后,如果您还等不到我回来取,您就可以打开它里面的东西,就全归您了如果我回来了,我必有重谢”他盯着石山根的眼睛,目光灼灼:“这件事,对我来说,比我的命还重要石大哥,我信得过你。
山里人的承诺,比石头还硬”石山根沉默了他掂了掂手里的包裹,感受着那异样的分量他看不懂眼前这个文弱的书生,也想不通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能感觉到,对方没有撒谎,那眼神里的沉重和期盼是装不出来的他想起了自己爷爷说过的话:山里人,可以穷,可以没文化,但不能没信用。
答应了狼不出圈,那就算饿死,也不能动套索“好”石山根吐出一个字“您要发誓”程援青坚持道石山根举起粗糙的右手,对着头顶那轮清冷的月亮和背后沉默的群山,沉声说道:“我石山根对山发誓,十年之内,不动这东西分毫。
如有违背,让山神爷收了我”听到这个誓言,程援青像是松了一口气,整个人的精神都垮了下来他深深地给石山根鞠了一躬第二天一早,石山根套上爬犁,亲自把程援青送到了三十里外的镇上临别时,程援青再次叮嘱:“石大哥,记住,十年之约。
”石山根点了点头,看着程援青一瘸一拐地消失在镇子尽头的拐角处他调转爬犁,重新回到了他的山里只是从那天起,他的生命里,多了一个沉甸甸的、无声的秘密第二章:无声的重量程援青走了,就像一阵风刮过,除了炕头上多出来的一床旧被褥和那个沉甸甸的油布包,没留下太多痕迹。
石山根把包裹藏在了自家炕洞的最深处,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凹槽里,外面用几块松动的砖头垒好,再抹上泥做完这一切,他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却空落落的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打猎,砍柴,侍弄房前屋后那一小块贫瘠的土地。
秀莲问过几次包裹里是什么,石山根只是闷着头说:“人家的东西,答应了不动,就不能动”次数多了,秀莲也就不问了她信自己的男人,他说的话,就是板上钉钉但这个秘密,就像一颗埋进土里的种子,在石山根心里悄悄发了芽。
夜深人静,听着窗外的风声,他会忍不住去想,那油布里到底裹着什么?金条?银元?还是一块传家宝玉?程援青那郑重其事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头一两年,这种好奇心还不算强烈石山根每天在山里奔波,累得沾枕头就着,没太多闲工夫去琢磨一件十年后才能揭晓的谜底。
他把这件事压在心底,就像把一块石头压在咸菜缸上,稳稳当当村里人只知道他救了个外地人,没人知道包裹的事只有住在村东头的福叔,一个爱嚼舌根的老光棍,时常拿这事打趣他“山根,我说你就是实心眼,”福叔坐在石山根家门口的石墩上,磕着瓜子,“救了个人,连个谢礼都没捞着?人家城里人,手指缝里漏点都够咱们吃半年的。
”石山根闷头磨着他的刀,不搭腔“要我说,那货郎就是个骗子,看你老实,给你画了个大饼十年?十年后黄花菜都凉了,谁还记得谁啊!”福叔把瓜子皮吐得老远石山根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看了福叔一眼,眼神像山里的潭水,深不见底。
“俺答应了”他说简单的三个字,让福叔碰了个钉子,悻悻地走了时间的流逝在深山里是缓慢而模糊的一棵树长高了多少,儿子虎子的个头蹿了多高,秀莲眼角的皱纹多了几条,这些就是石山根计算岁月的方式转眼到了八零年,已经是包裹被藏下的第四个年头。
这一年,山里遭了灾先是春旱,地里的苞谷苗还没长高就打了蔫好不容易盼来雨,又是一场连着下了一个月的阴雨,山洪把本就贫瘠的田地冲得一塌糊涂秋天,收成连往年的一半都不到更糟的是,秀莲病了起初只是咳嗽,后来发展到整夜整夜地咳,咳得胸口疼,人也迅速消瘦下去。
石山根采了山里能治咳嗽的草药,一锅锅地熬,却不见好转他背着秀莲去镇上的卫生院,医生检查了半天,开了些西药,说是肺上的毛病,得好好养着几包药片下肚,家底就空了秀莲的病却时好时坏,拖着,不见痊愈她心疼钱,说什么也不肯再去医院,每天躺在炕上,听着自己的咳嗽声,眼神一天比一天黯淡。
石山根心如刀绞他加倍地进山,想多打些猎物换钱可那年头,山里的野物也像是知道光景不好,躲得严严实实,他常常一整天都空手而归一个深夜,秀莲又咳得喘不上气,石山根给她拍着背,听着她微弱的喘息声,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从心底冒了出来——那个包裹。
如果里面是钱呢?是金条?只要拿出来一小块,就能给秀莲治病,能让她吃上好东西补补身子程援青说过,那是比他命还重要的东西,肯定价值不菲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压不下去了它像一条毒蛇,嘶嘶地吐着信子,缠绕着他的心脏。
他看着炕上病弱的妻子,又想起了那个对山神爷发下的毒誓一边是至亲的性命,一边是比石头还硬的承诺石山根这辈子,第一次感到如此煎熬他悄悄下了炕,走到炕洞边夜很静,只能听到秀莲压抑的咳嗽声和自己的心跳声,擂鼓一般。
他蹲下身,手指触碰到了那几块松动的砖头砖头冰凉,像是在提醒他那个冰冷的誓言只要把砖头挪开……他的手在发抖他这双能稳稳端起猎枪的手,此刻却抖得厉害脑海里,程援青那张苍白而郑重的脸和秀莲憔悴的面容在交替出现。
“山根……”炕上传来秀莲微弱的呼唤石山根浑身一震,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猛地缩回手,站起身,快步走到炕边“咋了?又不舒服了?”他柔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秀莲摇摇头,抓住他的手,她的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很温暖。
“别……别为我发愁我这是老毛病了,养养就好你明天……别进山了,雪大,路滑”石-山根握紧妻子的手,眼眶发热他点了点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一夜,他坐在炕边,守了秀莲一夜他再也没有朝那个炕洞看一眼天亮的时候,他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他没进山他去了村东头的福叔家,低声下气地借了二十块钱福叔虽然嘴碎,但心不坏,骂骂咧咧地把钱给了他然后,石山根又去了几家平日里关系还不错的邻居家,东拼西凑,凑了五十多块钱他把钱塞给秀莲,让她无论如何要去县医院好好看看。
秀莲拿着那一把零零碎碎、带着体温的钱,哭了钱最终还是没能彻底治好秀莲的病,但总算让她缓过了一口气日子,还在艰难地往下过而那个包裹,依旧静静地躺在黑暗的炕洞里它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了一个山里汉子最艰难的抉择。
它的重量,似乎比以前更沉了石山根知道,那沉的不是包裹本身,而是他扛在肩上的那个名为“承诺”的东西他扛住了,没被压垮第三章:山外的风八十年代的春风,像个迟到的信差,终于吹进了长白山的深沟险壑先是山下的公社解散了,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
接着,镇上出现了第一家“万元户”,是那个最早承包了果园的赵瘸子消息传到石山根他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就像往平静的水潭里扔了块大石头人们的眼睛开始发亮,谈论的话题不再是哪家分了多少粮食,而是谁谁谁在外面发了财。
山里人骨子里的那股子沉寂被搅动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石山根的生活也起了变化他不再是生产队的猎户,而是为自己打猎山货的价格一天一个样,一张好点的狐狸皮,能卖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价钱家里的光景,比前几年好了不少。
秀莲的病,在药物和充足营养的调理下,也渐渐稳定了下来,虽不能根除,但至少不再整日卧床儿子虎子,长成了半大小子,个头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往上蹿他不再满足于跟着石山根在山里转悠,他的眼睛总是望着山外他从镇上同学那里听来了太多新奇的东西:录音机、喇叭裤、香港的电影明星……那些东西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这个山里少年的心。
这一年,是程援青留下包裹的第七个年头石山根对那个包裹的念想,已经淡了很多生活有了盼头,人就不容易胡思乱想他甚至觉得,十年之约,不过是当年程援青为了让他心安理得收下谢礼而想出的一个说辞或许,那人早就不在了,又或者,早就把他这个山里的救命恩人忘得一干二净。
他还是会偶尔在深夜,手掌贴在炕洞的砖墙上,感受那份沉默的存在那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个提醒提醒他,自己曾许下过一个怎样的诺言然而,山外的风,终究还是吹乱了他平静的心虎子初中毕业,死活不肯再念下去了他想去南方,去那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深圳”。
“爹,我不像你,我不想一辈子困在这山里!”虎子梗着脖子,跟石山根顶撞,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父亲说话他穿着一件从镇上买来的牛仔外套,在他自己看来很时髦,在石山根看来却不伦不类“山里有什么不好?养活了你,养活了我,养活了咱们祖祖辈辈!”石山根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火星四溅。
“好?好在哪?一年到头就那么点收成,打猎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你看人家王二麻子,去广东打了两年工,回来就盖了砖瓦房!你再看看咱们家,还是这破木楞房!”虎子的话像刀子,扎在石山根心上“那是人家的本事,你有什么本事?你连山里的狼都斗不过,还想去跟外面的虎斗?”。
“我就是没本事才要出去闯!爹,你让我去吧,我保证,混不出个人样我绝不回来!”虎子的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焰,那是属于年轻人的、对未知世界的渴望石山根沉默了他看着儿子,仿佛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个体他不懂儿子嘴里的“闯”,在他看来,安安稳稳地守着这座山,就是最大的安稳。
父子俩的争吵,成了那段时间家里唯一的声音秀莲夹在中间,两头为难一天晚上,虎子又为了出去的事和石山根大吵一架,摔门而出石山根一个人坐在炕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屋里烟雾弥漫秀莲默默地收拾着碗筷,叹了口气,坐到他身边。
“山根,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你别太犟了”“他那叫想法?那叫瞎闯!外面的世界是那么好混的?”石...山根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秀莲犹豫了很久,才轻声说:“山根,要不……把那个包裹……打开看看?”石山根的身体猛地一僵,他转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婆娘。
这么多年,秀莲从未主动提过这件事“你……你说啥?”“我说,”秀莲鼓起勇气,直视着他的眼睛,“还有三年就到十年了那个程先生,七年都没消息,八成是不会回来了虎子想出去,总得有本钱要是……要是里面真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们就当是借他的,等他回来了,再还给他。
要是他不回来,那不正好给虎子用了吗?”秀莲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石山根心中那道尘封已久的门是啊,七年了人生有几个七年?那个叫程援青的货郎,或许真的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虎子,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未来。
这些年,村里人靠着各种门路,日子都越过越红火有人开了磨坊,有人养了长毛兔,有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只有他石山根,还守着这片山,守着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被人看作是“老顽固”、“不开窍”当虎子用那种近乎鄙夷的眼神看他时,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坚守产生了怀疑。
难道,为了一个外人的承诺,就要耽误自己儿子的前程吗?他的心,乱了那个包裹,不再仅仅是一个秘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旧的规矩和新的世界之间的冲突打开它,就意味着向儿子、向这个正在飞速变化的世界妥协不打开,就意味着继续坚守那份在别人看来早已过时、甚至有些可笑的道义。
他一夜无眠第二天,虎子回来了,眼睛红红的,显然在外面哭过他没再提去深圳的事,只是默默地帮着家里干活,但那股子消沉劲儿,谁都看得出来石山根看着儿子无精打采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晚上,他把虎子叫到跟前。
“你真想出去?”他问虎子点了点头,没说话石山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这些年他打猎攒下的所有积蓄,一共三百二十七块五毛“爹没本事,”石山根把钱推到儿子面前,“就这么多了你拿着,出去看看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山里总有你一口饭吃。
”虎子愣住了,他看着那堆被捏得发旧的毛票,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没想到,一向固执的父亲,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爹……”“去吧”石山根摆了摆手,转过身去,不再看他,“记住,在外面,别做亏心事,别忘了自己是山里石家的根。
”虎子走了带着那三百多块钱,和父亲的嘱托,踏上了南下的火车石山根站在村口的山坡上,望着儿子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山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走了他心里的一丝迷茫他最终没有打开那个包裹他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但他知道,有些东西,比钱财、比别人的看法更重要。
那是他石山根做人的根根要是断了,人也就站不住了山外的风,吹得再大,也吹不断这大山里的根第四章:一个人的影子虎子走了之后,木楞房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起初,石山根和秀莲还很不习惯,吃饭的时候总觉得少了一双碗筷,夜里也仿佛能听见隔壁房间传来虎子翻身的声响。
但时间是最好的抚平剂,日子久了,夫妻俩也渐渐适应了这种寂静虎子每隔一两个月会寄信回来,信里说着他在南方的见闻他说那里的高楼比山还高,夜晚亮得像白天,工厂里的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他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虽然辛苦,但每个月都能挣到比石山根一年打猎还多的钱。
信的末尾,他总会加上一句:“爹,娘,你们别担心,我在这边挺好的”石山根不识字,每次都是秀莲念给他听他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那微微上扬的弧度,却泄露了他内心的骄傲时间来到了八五年,距离十年之约,只剩下最后一年。
这些年,石山根的头发已经花白,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像刀刻的一样他依然每天进山,但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么轻快他开始觉得,自己老了那个关于包裹的秘密,已经被他埋藏得更深它不再是诱惑,也不再是负担,而是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部分,一个只有他自己能懂的坐标。
每当他在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里感到迷茫时,他就会想起那个承诺,心里便会多一份安定然而,就在这平静如水的日子里,一丝不寻常的涟漪悄然荡开那天,石山根去镇上卖皮货镇子比几年前繁华了许多,土路变成了石子路,路边盖起了两层的小楼,还开了一家“录像厅”,门口围着一群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他在供销社门口的收购点卖完东西,正准备去买点盐巴和烈酒,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个人那是个陌生人,穿着一身在当时看来非常体面的深灰色呢子大衣,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跟这个尘土飞扬的小镇格格不入他正站在供销社的布告栏前,似乎在看什么,但眼神却不时地扫过周围的人。
石山根心里“咯噔”一下不是因为这人的穿着,而是因为他的眼神那是一种审视和探寻的眼神,带着一种城市人才有的精明和警惕石山根没有声张,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旁边的杂货铺,要了一包烟,然后蹲在门口,一边抽烟,一边用眼角的余光观察那个男人。
只见那个男人跟供销社的售货员搭上了话,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出了名的嘴碎男人递上一根带过滤嘴的香烟,胖女人立刻眉开眼笑他们聊着什么,男人不时地用手比划着,像是在打听什么人石-山根的心跳,莫名地快了起来。
他想起了九年前,那个同样穿着干部服、同样带着一身山外气息的程援青难道……是来找他的?或者是……来找那个包裹的?这个念头让石山根的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九年了,他几乎已经把程援青当成了一个不会再出现的人可眼前这个陌生人,让他心底那根紧绷的弦,再次被拨动。
他不动声色地抽完一根烟,起身离开了他没有回村,而是绕到了镇子后面的小山坡上,那里可以俯瞰整个镇子的主干道他像一头经验丰富的老狼,潜伏在暗处,观察着猎物的动向果然,没过多久,那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从供销社里走了出来。
他没有离开镇子,而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眼睛却像鹰一样,仔细打量着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上了年纪的山里人石山根的心沉了下去这人,十有八九是在找人他没有再看下去,悄无声息地从另一条小路下了山,抄近道回了村。
回到家,他第一次主动打开了那个尘封的炕洞他把油布包裹拿了出来,抱在怀里包裹依旧沉重,油布的表面已经因为年深日久而变得有些发粘他摩挲着包裹的棱角,心里翻江倒海如果那人是程援青的朋友,他该不该把东西交出去?可程援青说过,要等他亲自来取,或者等到十年期满。
如果那人是程援青的仇人呢?当年的程援青,神色慌张,身负重伤,明显是在躲避什么把包裹交出去,会不会害了程援青?一个又一个问题,在他脑子里盘旋他发现,自己对程援青的过去一无所知,这个承诺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他无法想象的危险。
从那天起,石山根变得警惕起来他进山的时间少了,更多的时候,他会扛着猎枪,在村子周围的山头上转悠,像一头守护领地的孤狼他告诉秀莲,是山里的野猪最近不安分,怕它们下山毁了庄稼秀莲信以为真,只是觉得他最近的话更少了,眼神也变得比以前更加深邃。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后来又在镇上出现过两次石山根都远远地看见了他甚至有一次看到男人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往附近几个村子的方向去了,似乎是在挨个打听石山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开始担心,对方会不会找到自己村里来。
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有人找上门,他该如何应对他把那把砍刀,磨得更加锋利,放在了最顺手的地方这个承诺,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显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它不再仅仅是关于诚信和道义的考验,而可能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博弈。
石山根不害怕他在山里跟熊瞎子对峙过,跟狼群周旋过,死亡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他怕的是,自己守了九年的东西,最后却因为自己的失误,没能守住他成了一个背负着影子的独行者白天,他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夜晚,他抱着那个包裹,才能勉强入睡。
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九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那个叫程援青的男人,把一个沉重的、关乎性命的未来,交到了他的手上现在,离终点只剩一步之遥了他必须走完第五章:十年之约一九八六年的冬天,来得和十年前一样,带着一股子凛冽的寒气。
对于石山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冬天的到来,更是一个漫长约定的终点日历上的那个圈,他已经在心里画了无数遍就是今天,整整十年他起得很早,天还没亮窗外,北风呼啸,和十年前那个救人的日子一模一样石山根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侍弄牲口,而是打了一盆滚烫的热水,仔仔细细地洗了脸,刮了胡子。
他从箱底翻出了一件过年才舍得穿的蓝色卡其布上衣,虽然已经洗得发白,但很干净秀莲看着他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有些不解“山根,你这是……”“今天,是十年了”石山根的声音很平静,但秀莲能听出那平静下压抑着的某种情绪,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
秀莲一下子明白了她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帮他把衣服的褶皱抚平石山根走到炕洞边,他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感他没有丝毫犹豫,挪开砖头,从最深处,取出了那个油布包裹十年的光阴,让油布的颜色变得更加深沉,上面落满了灰尘。
石山根用袖子,一点一点,把灰尘擦拭干净,仿佛在擦拭一件稀世珍宝他把包裹端端正正地放在炕桌上秀莲给他倒了一碗酒,自己也倒了一碗夫妻俩没有说话,只是端起碗,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烈酒下肚,一股暖流从胃里升起,驱散了清晨的寒意,也壮了石山根的胆。
他坐下来,面对着那个包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手,那双布满老茧、能轻易捏碎核桃的手,此刻在微微颤抖他不是害怕,是激动这十年,他经历了贫穷、病痛、诱惑、怀疑和恐惧,这一切,都和眼前这个沉默的包裹紧紧地绑在一起。
今天,他终于可以亲手揭开这个谜底了他先是解开外面那层用麻绳捆扎的结,绳子已经有些糟朽然后,他开始剥离那层坚韧的油布油布被封得很死,边缘用蜡封住了,石山根只能用小刀一点点地割开随着“刺啦”一声,油布被彻底撕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没有金条,没有银元,也没有想象中的珠宝玉器最上面,是一个用蓝布包裹的小包袱打开包袱,里面是一块温润的、雕着麒麟图案的旧玉佩,玉色古朴,显然是有些年头的老物件玉佩下面,是一张泛黄的黑白全家福照片照片上,一个儒雅的中年男人和一个温婉的女人坐着,身后站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赫然就是十年前的程援青,只是那时的他,脸上还带着一丝属于年轻人的意气风发。
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隽秀的小字:一九六五年夏,于金陵旧宅在照片下面,是一沓厚厚的信纸,用细麻绳捆着信纸的纸张已经发脆,上面的字迹是用毛笔写的,笔力遒劲,内容似乎是日记或是一些文章石山根不识字,他把信纸递给秀莲。
秀莲念过几年书,能认得一些她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吃力地念着信里的内容,断断续续地为石山根拼凑出了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故事程援青,本名不叫程援青,他姓陆,叫陆泽远他的家庭,曾是金陵城里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
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让他的家庭瞬间倾覆父亲被批斗,母亲不堪受辱自尽,家被抄了,所有的藏书和手稿都被付之一炬这沓信纸,是父亲在被关押期间,偷偷写下的平反材料和一些未完成的学术手稿这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们陆家唯一的清白证明。
程援青(陆泽远)带着弟弟妹妹,怀揣着父亲拼死送出的手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他化名程援青,当过工人,下过乡,最后做了货郎,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罪证”保存下来十年前,他之所以会出现在长白山,是因为他得到消息,当年迫害他父亲的那些人,正在四处搜寻这些手稿,想要彻底销毁证据。
他走投无路,只能冒险穿越这片无人区,想去投奔一个远在东北边境的远房亲戚没想到,却在风雪中失足,差点丧命信的最后,陆泽远写道:“……将此物托付于石大哥,实乃无奈之举我观其人,面冷心热,眼神清澈,有山之风骨,是可托付性命之人。
十年之约,非我故弄玄虚十年之内,风波未平,此物现世,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唯有等待,等待云开雾散之日若十年后我未归,望石大哥将此物妥善处置,或焚于山中,或沉于江底,切勿示人陆家之冤屈,已不重要,万不可因此连累恩公……”。
读到这里,秀莲的声音已经哽咽石山根沉默地坐着,像一尊石像他终于明白了他守了十年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家庭的清白,一个学者的尊严,和一个儿子沉甸甸的孝心这个包裹的重量,远比他想象的要重得多他拿起那张全家福,照片上的一家人,笑得那么温和。
他仿佛能看到,这个叫陆泽远的年轻人,是如何背负着这一切,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艰难地活下来的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踏雪的脚步声石山根的身体瞬间绷紧,他下意识地把桌上的东西拢到怀里,另一只手摸向了身边的猎枪。
脚步声在门口停下,随即,响起了三下叩门声,不轻不重,很有节奏“谁?”石山根沉声问道门外传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激动:“请问……这里是石山根,石大哥的家吗?”石山根和秀莲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震惊。
这个声音……石山根慢慢站起身,一步步走到门前,拉开了门栓门外,站着一个男人他穿着一件得体的黑色大衣,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虽然眼角已经有了风霜的痕迹,但那张脸,那双眼睛,石山根一辈子也忘不了正是程援青——不,是陆泽远。
他的身后,停着一辆黑色的、石山根只在电影里见过的轿车四目相对,十年光阴,仿佛在这一刻被压缩成了一个瞬间陆泽远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身形却依然挺拔如松的猎人,嘴唇哆嗦着,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声哽咽的呼唤:。
“石大哥……我回来了”第六章:不曾变过的山陆泽远站在门口,风雪吹在他的肩上,他却浑然不觉他的目光,越过石山根的肩膀,落在了屋里炕桌上那摊开的信纸和熟悉的油布上他的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石山根侧过身,把他让了进来。
“外面冷,进屋说”他的声音,还和十年前一样,沉稳,听不出太多波澜屋里的火炕烧得正旺,暖意瞬间包裹了陆泽远他脱下大衣,露出了里面合身的毛衣他不再是当年那个狼狈的货郎,眉宇间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和成功人士的从容,但那份书卷气,却丝毫未减。
秀莲给他倒了一碗热茶,他双手接过,连声道谢“石大哥,大嫂,”陆泽远捧着热茶,看着眼前这对容颜苍老的夫妻,眼中的感激和愧疚交织在一起,“这些年……让你们受累了”“人没事就好”石山根指了指桌上的东西,“约定的日子到了,我刚打开。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这些东西,我可能就真按你信里说的,烧了”陆泽远闻言,苦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知道您一定会遵守诺言所以我才敢今天来”他放下茶碗,郑重地说道,“石大哥,我的事,都解决了父亲的冤屈,得到了平反。
那些手稿,现在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我这次来,一是来取回信物,二是……来报恩”他说着,从随身的提包里,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了桌上,推到石山根面前“石大哥,这里是一万块钱我知道,这点钱,根本无法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和这十年的守护之情。
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和嫂子,还有虎子,可以用这笔钱盖个新房,做点小生意,让日子过得好一些”一万块钱在八十年代的这个小山村,这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足够盖起十座青砖大瓦房秀莲倒吸了一口凉气,下意识地看向石山根。
石山根的目光,却落在那叠钱上,眉头微微皱起他没有去看钱,而是看着陆泽远,缓缓地摇了摇头“陆先生,”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你弄错了”陆泽远一愣:“石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条人命,倒在我家门口,我不能不救。
我守着这个包裹,是因为我石山根对山神爷发过誓,答应了你十年”石山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屋里每个人的心上他把那个信封,又推了回去“一码归一码救命,是山里的规矩守诺,是我做人的规矩这两件事,都和钱没关系。
”陆泽远的表情凝固了他没想到,自己设想了无数次的报恩场景,会被这样一句朴实无华的话,堵了回去他急切地说道:“可是,石大哥,这十年,你们过得那么苦!我听说了,大嫂生病,虎子上学……如果你们当时打开了包裹……”。
“没有如果”石山根打断了他,“打开了,就不是我石山根了”他拿起桌上那块麒麟玉佩,和那张全家福,递给陆泽远“你的东西,你拿好完璧归赵咱们之间的约定,就算完成了”陆泽远捧着那块失而复得的家族信物,手在颤抖他看着眼前这个固执得像一块石头的山里汉子,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明白了,有些东西,确实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比如,一个人的风骨和尊严他不再坚持,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着石山根和秀莲,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石大哥,大嫂,我陆泽远……受教了”那天中午,秀莲做了一桌子菜陆泽远和石山根喝了很多酒。
陆泽远讲了他这十年的经历,如何辗转找到当年的证人,如何一层层地递交材料,最终沉冤得雪他也讲了自己下海经商,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石山根默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给他满上酒临走时,陆泽远没有再提钱的事他从车里,拎出了一把崭新的猎枪,枪身乌黑锃亮,还配着一个高倍的瞄准镜。
“石大哥,钱你不要,这个你得收下”陆泽远把枪塞到石山根手里,“你是猎人,枪就是你的第二条命这把枪,比你那把老伙计好用就当是……一个朋友,送给另一个朋友的礼物”这一次,石山根没有拒绝他摩挲着冰冷的枪身,点了点头。
黑色的轿车,在雪地里缓缓驶离,最终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石山根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把新猎枪,站了很久秀莲走出来,给他披上一件棉袄“他是个好人”秀莲说“嗯”石山根应了一声他抬起头,望向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大雪过后,山峦被白雪覆盖,在阳光下,泛着圣洁的光芒。
这十年,山下的小镇变了样,人们的穿着、想法、生活方式都变了,连他的儿子,也成了他不再熟悉的“城里人”整个世界,都在飞速地变化着只有这座山,不曾变过它依然沉默,依然威严,依然用它自己的规矩,衡量着世间万物。
石山根觉得,自己就像这座山里的一棵树,一块石头外界的风,吹得再猛,也只能吹动他的枝叶,却动摇不了他的根他握紧了手里的猎枪,转身回屋生活,还要继续那个持续了十年的秘密,已经画上了句号但那个关于承诺和坚守的故事,已经刻进了他的生命里,成了他骨头的一部分。
他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