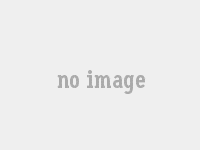被哥嫂卖给克妻老光棍那夜,我跳窗逃进深山,一头栽进了雪窝子
《冷脸糙汉》被哥嫂卖给克妻老光棍那夜,我跳窗逃进深山,一头栽进了雪窝子醒来时,冷脸糙汉正往我嘴里灌红糖水,耳尖红得像山柿子我扯谎卖惨求收留,他却连夜缝了狐皮袄子给我当嫁妆后来我作天作地闹离婚,他反手甩出一张泛黄的卖身契,落款竟是八年前我随手救下的落水少年。
原来这男人早就把自己当成债抵给了我,利息是每天多亲一口当城里的知青嘲讽他穷酸时,我晃着孕肚冷笑:「我男人猎的狐狸能铺满炕,糙汉的快乐,你不懂」回家的时候,我贴着他发烫的耳垂呢喃:「赵跃进,你比狐狸还会缠人。
」他低笑着咬我的指尖:「缠你一辈子。」

1腊月二十三,天黑时飘起了鹅毛大雪我缩在漏风的偏房里,听见了嫂子在堂屋里尖着嗓子叫骂「吃白饭的赔钱货,明儿就送你去王家!」炕桌上的玉米糊早就凉透了,我捏着豁口碗的手直哆嗦王家那老光棍克死三个媳妇的传言,早就成了村里人饭桌上的谈资。
雪花扑簌簌地砸在窗棂上时,我踩着条凳翻出了婚房的木窗棉鞋陷进雪窝子里,寒气顺着脚底板直接窜上了天灵盖跑了约莫半个钟头,前头黑黢黢的山影晃成了重影我栽进雪堆时还在想,冻死也比被老光棍克死强再睁眼时,鼻子先嗅到了柴火混着艾草的焦苦味。
粗布被面硌着脸,我猛地掀开被子,衣裳倒是齐整,就是裤脚结着冰碴子木门吱呀一声响,撞进来个高大的身影「喝」粗陶碗怼到眼前,蒸腾的热气糊了我满脸男人裹着件褪色的军大衣,眉骨上还横着道疤我攥着被角往后缩:「你……你是王家派来的?」。
他耳尖倏地红了,碗沿重重地磕在炕桌上:「红糖水,趁热,快喝」说完,他转身要走时又顿住了,从裤兜掏出个油纸包,「灶上煨着粥」纸包里躺着三块桃酥我盯着他青筋凸起的手背,忽然哽着嗓子哭出声:「哥,你叫啥?我哥嫂要把我卖给五十多的老光棍……」。
眼泪珠子不要钱似的往下砸,其实五分真五分假闻言,他沉默了半晌才闷声说:「赵跃进」「赵大哥,我没处去了」我抹着眼泪偷瞄他,「我洗衣做饭都会,能跟你搭伙过日子不?」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两滚,也没说什么,摔门走了。
没过一会儿,灶房传来哐啷啷的响动,我赤着脚扒在门缝上看他抡斧头劈柴的胳膊筋肉虬结,火星子溅在了翻毛靴面上铁锅里咕嘟着白菜汤,案板上忽然多了颗鸡蛋我惊讶地看着这颗鸡蛋,毕竟这年头鸡蛋金贵,我哥嫂都锁在橱柜最里头。
「端着」他板着脸把海碗撂在炕桌上,金灿灿的蛋花浮在清汤上,底下沉着细白的面条我捧着碗暖手,看他蹲在门槛上啃冷窝头夜里的北风撞得窗纸哗啦啦地响,我裹着棉被打摆子外间传来窸窣响动,赵跃进抱着捆麦秸进来铺地铺。
月光漏进来时,照见了他腕上结痂的冻疮我鬼使神差伸手拽了一下他的袖口:「炕这么大,分你一半?」他触电似的甩开我的手,军大衣擦着我的鼻尖掠过门板砰地撞在土墙上,院里传来劈柴声,一下比一下狠,震得房梁都在抖我缩在被窝里数窗纸破洞外的星星,灶膛里的火噼啪爆响。
天蒙蒙亮时,门缝塞进来双毛毡靴,鞋帮上还沾着露水我扒着窗棂往外瞧,赵跃进扛着猎枪往山里去了灶台上温着玉米面饼,瓦罐里居然有勺猪油我蘸着饼子啃时,瞥见墙上挂着一张硝好的狐狸皮,雪白的毛尖泛着银光昨儿夜里,这皮子就盖在了我的身上。
2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外间铁锅磕碰的响动吵醒了赵跃进回来了他军大衣的肩头上落满了霜花,怀里却揣着热乎的烤地瓜见我醒后,他把那块热乎乎的烤地瓜塞给了我「晌午炖山鸡」说完,他把滴血的麻袋扔在灶台边,山鸡尾羽扫过我的手背,痒得我直躲。
他忽然扔过来个油纸包我剥开三层糙纸,发现里头竟躺着两颗水果糖上回吃糖还是在娘走那年,我把糖块含在腮帮子左边,鼓着脸冲他笑:「赵大哥也吃一颗?」他耳尖腾地红了,「哄小孩的玩意儿」说完,他转身就去院里劈柴,斧头抡得虎虎生风。
我蹑手蹑脚把糖纸夹进笔记本没过一会儿,铁锅就咕嘟着喷香的肉味儿我端着陶碗偷摸往他的碗底藏了一只鸡腿,却被他筷子一翻,油汪汪的肉又落回了我碗里「你瘦得跟鹌鹑似的,你吃吧」他闷头啃着贴饼子,玉米面渣沾在嘴角。
夜里又飘起了雪我裹着棉被看他补渔网土炕烧得太烫,我故意把冰凉的脚丫子贴着他的小腿肚:「赵大哥,给我焐焐脚呗?」他猛地弹了起来,后脑勺撞得房梁扑簌簌地落灰渔网缠住了解放鞋,他踉跄着扶住门框才没摔倒「我去瞅瞅篱笆。
」他抄起蓑衣就往外冲我在炕上笑得打滚,忽然摸到他坐过的草席还留着体温后半夜,我抱着枕头摸进外屋,正好撞见他赤着上身擦药酒,腰腹的肌肉绷成了一块块山岩,旧伤疤像蜈蚣一样爬过麦色的皮肤我俩大眼瞪小眼地僵在原地,他慌得扯过棉被裹成了大粽子。
「炕……炕塌了」我扯谎都不打草稿,泥鳅似的往他被窝里钻他身上有股松针混着艾草的味道,熏得我鼻子发酸他浑身绷紧,哑着嗓子低吼:「张爱华!」我趁机搂住他的脖子,脸贴着他鼓动的喉结:「炕都塌了,我没地方睡了」。
外头的雪越下越大,他僵硬地背过身去躺下,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虽然隔着两层两床被子,但他的心跳声震得我耳膜发麻晌午的时候,他扛回半扇野猪肉,村口的王婶扒着篱笆偷瞄:「赵猎户如今开荤了?」他抄起砍刀剁得案板砰砰响,肉沫子飞溅到王婶的衣襟上:「眼馋让你家汉子进山啊。
」我憋着笑给他盛杂粮饭,他忽然从兜里掏出个铁皮盒推过来盒盖上红双喜都磨花了,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十二颗水果糖「供销社新到的」说完,他扒饭的速度比往常都快了一倍夜里我故意把糖块咬得咔咔响,他翻来覆去烙饼似的折腾草席。
灶膛火星噼啪炸响,我数着他鼾声的节拍往那边蹭指尖刚碰到他粗粝的手心,突然被他攥住手腕按在草席上他的呼吸喷在我的额角上发烫:「再闹腾,明儿把你拴裤腰带上山!」我挣开他的手,把冰凉的脚丫子塞进他的胳肢窝:「那你可得把我焐热乎了。
」他倒吸冷气的声音混着夜风,惊醒了檐下打盹的麻雀3霜降那日我蹲在灶台边剥栗子,瞅见赵跃进扛着麻袋进门他抖开麻袋的瞬间,一蓬雪雾扑了我满脸里头躺着张火红的狐狸皮,油亮的毛尖还沾着晨露「硝好了给你做袄子」他拿草绳量我的肩宽,粗粝的指节擦过我后颈时,我冷不丁打了个颤。
狐狸皮上突然滚下一颗带血的狼牙,我捏着往他眼前晃:「定情信物?」他劈手夺过狼牙,耳根烧得比狐毛还红:「猎户辟邪的」说完,他又转身去院里支晾杆我摸着温热的皮毛偷笑,这颜色分明是母狐狸,哪用得着辟邪晌午炖了野山菌,他捧着海碗蹲门槛上喝汤。
我眼尖瞥见他的虎口处裂着血口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咋弄的?」他挣了两下没甩开,闷声说:「剥皮刀划的」药匣子里的红汞早结了块,我撕了块里衣给他包扎我忽然想起那夜摸到的腰腹伤疤,手一抖打了个死结他忽然反手握住我的手腕,喉结滚了滚:「张爱华,山里汉子的手都这样。
」我故意把指尖戳进他的裂口:「赵跃进,你疼不疼啊?」他猛地抽回手,汤碗咣当砸在了青石板上,油花溅湿了裤脚我蹲着捡碎瓷片,后颈突然罩上一片阴影他不知从哪掏出双羊皮手套,粗声粗气地扔在我的膝头:「省得扎手」。
晚上,我窝在炕头缝狐皮袄赵跃进在火塘边磨猎刀,火星子噼啪地蹦到草席上他忽然闷哼一声,刀尖在拇指划出一道血线我扑过去吮住伤口时,他整个人僵成了冰柱子「小时候我娘都这么止血」我舌尖尝到铁锈味时,抬头正好撞见他幽深的眸子。
火光照亮他滚动的喉结,我鬼使神差地凑近他的下巴:「赵跃进,你要不要媳妇?」猎刀当啷掉在地上,他掐着我的腰按进干草堆,麦秸秆扎得我的后背生疼滚烫的呼吸喷在我的耳际,我等着他亲下来,他却突然松了手:「你分得清感激和喜欢吗?」。
我揪着他的衣领不撒手,鼻尖抵着他突突跳的颈动脉:「那你教我分啊」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突然抄起炕头的狐皮裹住我,打横抱起来往西屋走我缩在他的怀里数心跳,数到二十七下时被扔进了冷被窝「睡你的觉!」他摔门的声音震得房梁落灰,我裹着狐皮数窗外的雪花。
三更天时,听见外间的水缸响,我扒着门缝偷看他赤膊站在院里浇冷水,脊背上蜿蜒的旧疤泛着青光,像条盘踞在山岩上的白蟒第二天他天不亮就进山了,晌午又扛回头瘸腿的麂子我蹲着给他递砍刀,瞥见手套破洞里渗着血丝夜里我揣着针线溜进他屋,他正对着油灯挑手心的木刺,见我进来慌忙藏起了手。
「躲啥?」我掐着他腕子按在炕桌上,就着昏黄的灯穿针引线他手心的纹路里嵌着黑泥,我拿缝衣针一点点挑,挑着挑着眼泪就砸在他的虎口:「赵跃进,你是不是傻?」他突然用带茧的拇指抹我眼角:「哭个屁」说完,转身就从炕柜里掏出个布包,抖开是件簇新的红棉袄,「开春穿。
」我摸着盘扣上歪扭的针脚,突然扑进他怀里咬他的锁骨:「你这算不算下聘?」他托着我后脑勺按在胸口,「张爱华,跟着我只有山风野味……」「我就要山风野味!」我踮脚吻上了他的唇,「还要你这个傻猎户」他猛地把我抵在土墙上,鼻尖蹭着我冻红的耳垂:「现在后悔还……」。
我没让他说完,仰头咬住他的下唇火塘爆了个火星子,惊醒了梁上打盹的狸花猫五更天的梆子响时,他忽然握住我的脚踝,往他结着冰碴子的胸口贴:「你不是说冷吗?这样还冷吗?」我踹他精壮的腰:「赵跃进,你这叫趁火打劫!」。
他低笑着咬我肩头,新长的胡茬扎得我生疼:「昨儿谁说要当压寨夫人?」天亮时,我摸到他后背新添的抓痕,突然想起那张火红的狐狸皮原来最会诱人入套的,从来不是山里的狐狸4立春那日,供销社门口的冰溜子化得滴滴答答。
我攥着肉票排队割五花肉,忽听见身后「咔嗒」一声脆响穿呢子大衣的姑娘蹬着小皮鞋,红围巾衬得脸蛋跟雪团子似的白她指尖捏着块梅花表,笑盈盈地问售货员:「赵跃进同志住哪片?」我手里的搪瓷盆咣当一下砸在了水泥地上。
那姑娘转头时,胸前的钢笔尖晃着银光我认得这牌子,上回在村长家见过,说是省城大官才用得起的「英雄 100」回家后,我在灶台边上炖着酸菜粉条,赵跃进扛着半扇狍子进门我故意把菜刀剁得震天响:「晌午有贵客,穿呢子大衣戴梅花表的。
」他擦猎枪的手一顿,枪油蹭在粗布裤上晕开了一片黑斑我们刚要吃饭,吴秋杏就进来了她把牛皮纸包着的两罐麦乳精搁在了炕桌上,摘羊皮手套的姿势像戏台子上的角儿,还露出腕间金灿灿的表链:「赵哥,伯父托我带话,机械厂主任的位置给你留着。
」我蹲在灶坑添柴火,火星子一下子蹦到了手背上赵跃进把狍子肉全拨进了我的碗里,眼皮都不抬一下:「我不去,山里待惯了」吴秋杏涂着丹蔻的指甲叩了叩麦乳精罐子:「住这破屋子,怎么配得上你?」「啪!」我摔了筷子,酸菜汤溅到了吴秋杏的呢子衣摆上。
赵跃进突然攥住我的手腕,「我媳妇怕生,你回吧」吴秋杏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摔门而去我扒着窗棂看她的小轿车突突地冒黑烟,笑出了声这时,我突然被掐着腰按在了炕沿上赵跃进咬着我的耳垂冷笑:「出息了,敢摔我买的筷子?」。
「那你跟她走啊!」我狠狠地踹了一脚他的小腿骨,「省得跟着我啃窝头!」他直接把我扛上肩头,军大衣裹着就往山里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停在了山神庙的后头,把我抵在老槐树上亲得喘不过气「机械厂算个屁。
」他啃着我的锁骨含糊道,「老子的猎枪值三头牛」我揪着他的头发往后扯,「那你爹……」「早当他死了」他突然托着我屁股往上颠,吓得我双腿紧紧地缠住他的腰山风卷着雪花往领口钻,他滚烫的手心贴着我的后腰:「冷就抱紧点。
」夜半听见外间的窸窣响声,我光脚溜到了门缝边赵跃进蹲在灶台前烧东西,火舌舔着张泛黄的照片一位穿着中山装的女人抱着个男娃,那男娃的模样与他七分像灰烬飘到我跟前时,他从背后把我裹进大衣里:「乱跑什么?」「你娘?」
我摸着照片残角他下颌抵在我的发顶嗯了声,呼吸喷得我头皮发麻:「十二岁发高烧,她背我走二十里山路,摔死在了冰窟窿里」我转身咬他的唇,「赵跃进,我给你生个娃吧?」话音刚落,他突然打横抱起我往炕上扔,扯棉被裹成蚕蛹:「先把你这二两肉养肥再说。
」第三天,吴秋杏又来了这次她带着一封盖红戳的介绍信我正在院里晾鹿皮,她的高跟鞋碾过晒着的山核桃,径直走向赵跃进:「赵哥,伯父说只要你回去,立刻安排工农兵大学的名额给你」赵跃进抡起斧头劈柴,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去,你以后别来了,我媳妇不喜欢生人。
」我憋着笑往他背后躲,被他反手塞了把炒松子那夜,他格外凶,在我的锁骨上咬出了一圈牙印我疼得挠他的后背:「赵跃进,你属狗的啊?」他喘着粗气抵进来,汗珠子砸在我的眼皮上:「张爱华,老子恨不得把你揣兜里」五更天时飘起了雨夹雪,我摸黑给他补棉裤。
吴秋杏塞在门缝的信被雨泡糊了,但还是能隐约看见「婚姻」、「前途」几个字赵跃进晨猎回来时,我正蹲在灶坑烧信,火舌卷着「赵家」俩字化成了灰「吃蛋羹」他忽然从兜里掏出个搪瓷缸,嫩黄的蛋液颤巍巍晃着香油花供销社这个月压根没鸡蛋票,我舀着蛋羹突然呛出了泪。
他的手背上新添了道血口子,怕是连夜掏了山雀窝晌午的时候,吴秋杏又来了这一次,赵跃进连门都没有给她开我笑着坐在院子里看赵跃进在篱笆外埋兽夹他发现我在偷看他后,转头就把我按在晾衣绳上亲:「还没看够?」晾着的红肚兜晃悠悠地遮住了日头,惊飞了檐下啄食的麻雀。
夜里,他翻出压箱底的狐皮袄给我裹上,自己穿着单褂子练瞄准我扒着窗台啃冻梨,看他脖颈结着霜还嘴硬:「火气旺,冻不着」后半夜我偷偷地把炕烧得滚烫,他被热醒时军衣都汗透了我趁机钻进他怀里,脚丫子蹭着他的小腿:「赵主任,机械厂有这热乎炕吗?」。
他掐着我腰的手猛地收紧,狠狠地咬住了我的唇:「叫男人!」山风卷着雪花拍打着窗户纸,我把脸埋在他汗湿的胸膛想:去他娘的机械厂,这山沟沟里,藏着我的金山银山呢5惊蛰刚过,山坳里的野桃树就爆了满枝的花骨朵我蹲在溪边捶打床单,泡沫顺着指缝往下淌,忽然听见村口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这回不是吴秋杏的小轿车,而是辆绿皮吉普,车轱辘碾得碎石乱蹦赵跃进正在院里剥鹿皮,猎刀悬在指尖上陡然顿住车门摔得山响,下来个穿中山装的老头,眉眼与他像是一个模子刻的,后头还跟着俩壮汉,胳膊比我腰还粗「畜生!」
老头杵着文明棍戳地,唾沫星子喷到晾着的红辣椒上,「赵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赵跃进低着头一言不发,鹿皮攥出了深紫的指印我抡起捶衣棒冲过去,木盆里的肥皂水泼了老头一裤腿「哪来的疯狗乱吠?」我把赵跃进拽到身后,湿漉漉的衣摆往下滴水,「我男人是顶天立地的猎户,比你们这些喝人血的强百倍!」。
老头抡起文明棍要抽,被赵跃进一把攥住腕子「滚」他声儿比三九天的冰溜子还冷,老头的腕子被捏得咯咯响俩壮汉刚要扑上来,赵跃进突然抄起墙角的猎枪,枪管顶在老头下巴颏:「十二年前你把我娘撵出家门时,怎么不说我是赵家人?」。
吉普车突突冒着黑烟逃了,我这才发现赵跃进虎口裂了口子,血珠子顺着枪托往下淌他蹲在灶台边擦枪,我蘸着烧酒给他消毒,棉签戳到伤口时他睫毛直颤:「疼就喊」「你方才挺凶」他突然攥住我手腕,眼底泛着血丝,「不怕我真崩了他?」。
我咬开酒瓶塞子往他伤口倒:「你敢崩,我就敢给你送牢饭」他低笑着把我拽进怀里,鼻尖蹭着我发顶的皂角香后半夜雷声隆隆,我摸黑去关窗,瞥见赵跃进蹲在柴垛旁烧东西,是那张硝了一半的鹿皮,火舌卷着皮毛蜷成了焦炭我从背后搂住他,脸贴着他冰凉的脊梁骨:「可惜了,能做双好靴子。
」他忽然转身把我按进草堆,草屑扎得我脖颈发痒:「张爱华,我娘是地主家的丫鬟」「她怀着我被撵出来,临死前还攥着把银锁,上面刻着赵家的族徽」我摸到他颈间冰凉的银链子,锁片上的蟠龙纹早磨平了棱角:「值钱吗?赶明儿熔了打对耳环。
」他掐着我腰的手突然收紧,闷笑震得胸腔发颤:「财迷」天还没亮,柴门又被拍得哐哐响我抄起烧火棍开门,一开门却发现是村东头的王媒婆,她挎着竹篮直往院里瞅:「赵猎户在吗?谭家闺女相中他打猎的手艺……」「相中他夜里打猎的手艺吧?」。
我杵着烧火棍冷笑,「回去告诉谭小翠,再敢往这送鞋垫,我拿狼牙给她纳双寿鞋!」王媒婆吓得竹篮都扔了,碎鸡蛋糊了满门槛赵跃进扛着野猪回来时,我正在刮门槛上的蛋壳他忽然从麻袋里掏出个布包,抖开是件水红的确良衬衫:「供销社扯的布。
」我摸着滑溜溜的料子撇嘴:「穿上就像个耍猴戏的」「比粗布软和」他耳尖泛红,蹲着削竹签串肉我故意把衬衫往他身上比:「你穿上更俊」他突然拦腰把我扛上肩头,「皮痒了?」半夜我数着他后背的疤,忽然摸到一块月牙形的旧伤:「这是咋弄的?」。
「十四岁掏狼崽,让母狼咬的」他翻身压住我作乱的手,「再乱摸,让你三天下不了炕」我咬着他的喉结含混道:「赵跃进,你这些疤比族徽金贵多了」五更天时落起了雨,我被柴火的噼啪声吵醒赵跃进蹲在火塘边煨红薯,火星子映亮了他新刮的下巴。
我裹着狐皮袄贴了上去他笑了笑,「等开春带你去上坟」雨点子砸在窗户纸上,我在他手心画圈:「你要跟娘说啥?」他忽然托着我的后颈深吻,红薯烤焦的煳味弥漫开来:「说捡了个泼辣媳妇,比山魈还凶」天亮的时候,我们分吃了焦黑的红薯芯,苦味儿在舌尖漫开,竟比麦乳精还甜。
晌午头修篱笆时,吉普车又碾着泥坑来了老头隔着车窗扔出个布包,砸在赵跃进的脚边散开是一摞泛黄的地契我抡起铁锹要拍车窗,却被赵跃进拦腰抱住:「别拍,脏了你的手」布包被他扔进了灶坑,火舌蹿得老高我扒着窗台看吉普车逃窜的尾气,忽然被他咬住耳垂:「张爱华,老子现在最大的产业……」。
他引着我的手按在怦跳的胸口,「在这儿。」